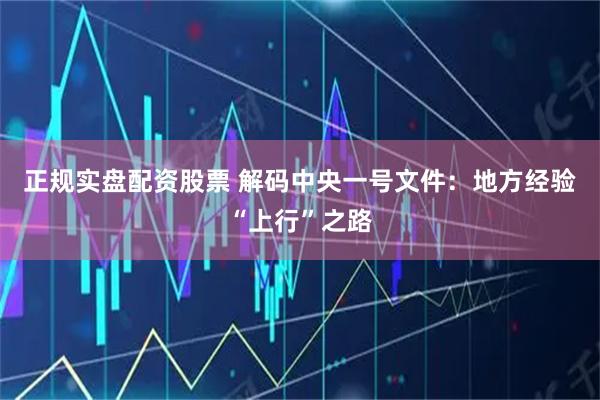

▲2026年2月4日,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峨山镇城东村,藕农采收鲜藕。(视觉中国/图)
全文共5214字,阅读大约需要10分钟
中央一号文件整个起草过程主要包括确定主题、调查研究、起草文稿、审议通过这四个环节。调研过程中,着重发现新问题,确定哪些做法能最终被写进文件,“有些内容即便确定了,还可能再次调研”。
地方经验“上行”之路从不单一,它们从四面八方汇入,经中央“去情景、提内核、再抽象”,最终淬炼为国家政策文本。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
文|南方周末记者 杜茂林
“十五五”期间首个中央一号文件,于2026年2月3日公布,主题依然锁定乡村全面振兴。
农业界形象地将中央一号文件称作“天字一号”。自1982年起,中央一号文件连续5年聚焦“三农”。中断17年后,2004年开始,已连续23年未离开这一主题。
“虽然只是排序问题,但却是信号、导向和标志。排到一号和最后一号影响肯定不一样。体现了中央对‘三农’工作的重视。”一位曾参与中央一号文件起草工作的学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出现了不少来自地方的做法。其中,“农创客”一词就是首次出现。文件提出:“加强乡村产业带头人和乡村治理人才培育,因地制宜培育农创客。”
农创客指年龄在45周岁以下,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在农业领域创业创新并担任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负责人或拥有股权的人员。据潮新闻报道,2015年,浙江在全国率先提出“农创客”。彼时,美丽乡村建设走在全国前列的浙江,提出要打造一支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型的农创客队伍。
多位“三农”学者总结中央一号文件的特点时都提到,如提出培育“农创客”一样,文件中不少被视为“顶层设计”的表述,往往有着清晰的地方来路,某些在基层反复尝试、修正甚至碰壁的做法,最终被谨慎规范的语言吸收进中央一号文件,成为全国的政策参照。
1
筛选和重构
前述参与过中央一号文件起草工作的学者注意到,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出现了“常态化精准帮扶”的新提法。中国已走过脱贫攻坚期,2021后进入5年过渡期。2026年,中央明确提出常态化,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基础上,实现小调整。
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中央一号文件在提及常态化精准帮扶时,还提出深入开展医疗、教育干部人才“组团式”帮扶和科技特派团选派。
据中国日报网消息,科技特派员制度也来自地方实践,源头在福建南平。早在1990年代中后期,当地就开始探索这一模式。此后各地不断发展完善,逐步形成科技特派团制度,在脱贫攻坚中发挥重要作用。
如农创客、科技特派团制度一样,能被写进中央一号文件的,通常都要经过漫长的试错与打磨。
浙江桐乡的“三治”(德治、法治、自治)试验,走过5年之后,被写进中央一号文件。
推动“三治”建设始于2013年。时任桐乡市委书记卢跃东提出四大奋斗目标,社会治理要一流就是其中之一。
卢跃东在乡镇基层干过8年。他发现,经济越发达的地方,社会治理问题越突出。产业集聚、人口流入、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叠加,让原本靠行政力量就能应付的基层事务,迅速变得棘手起来。
时任桐乡市市长盛勇军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直言,如果靠政府“大包大揽”,肯定“管不过来”。
两人商量后,决定创新一种新型社会治理模式,提出德治、法治、自治“三治”合一。
最初的试点被拆分到3个乡镇推行:一个镇抓德治,一个镇抓法治,一个镇抓自治。不到一个月,问题就暴露了。当地干部意识到,“三治”本是相互作用,相辅相成,分开不行。
桐乡迅速调整思路,将三种治理方式重新合并,集中到高桥镇这个矛盾最密集的地方进行试验。高桥镇位于城乡接合部,高铁建设带来的拆迁问题,使它成为各种利益冲突的交汇点。
2018年,桐乡“三治”做法被明确写进中央一号文件。在被中央文件吸纳过程中,省领导的支持和重视至关重要。
卢跃东曾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时任浙江省委副书记王辉忠到桐乡调研时,他就向王辉忠提出了“三治”的初步想法。王辉忠当即拍板,可大胆进行尝试、探索。
与桐乡同属浙江的县级市瑞安,也有改革经验被写进中央一号文件。
2005年4月,在清华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的陈林被引进到瑞安市,挂任副市长。上任不久,他开始筹建瑞安农村合作协会及其信合联盟——旨在打破长期以来农村信用合作、供销合作、农民专业合作彼此封闭、自我发展的割裂状态。这一想法,后来被概括为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的合作经济新路径。
瑞安的做法引起了时任省领导的注意。2006年10月,陈林被点名赴杭州汇报“三位一体”的做法。
之后,温州市、浙江省先后在瑞安召开现场会,推广“三位一体”试点经验。11年后,2017年,“三位一体”改革被写进中央一号文件。
此时,陈林已结束挂职,离开瑞安近10年。尽管如此,跳出浙江的他,仍在继续研究推广浙江经验。
陈林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三位一体”在被写进中央一号文件前,有中央部门领导多次到浙江调研、开座谈会,了解情况。
文件吸纳地方经验,离不开专家学者的深度参与。前述不愿具名的学者称,概括起来,中央一号文件整个起草过程主要包括确定主题、调查研究、起草文稿、审议通过这四个环节。调研过程中,着重发现新问题,确定哪些做法能最终被写进文件,“有些内容即便确定了,还可能再次调研”。
这位学者补充解释道,而那些最终被写进中央一号文件的地方经验,往往已历经多轮筛选和重构,有些经验很难简单说源自哪个具体地方。

2025年12月5日,江苏省泗洪县孙园镇一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借助大型喷灌机械开展小麦抗旱保苗。(视觉中国/供图)
2
相同做法,不同表述
从地方试验到最终上升为政策、制度,既有内部创新的反复试错,也有外部复杂的博弈。这导致同样的做法在不同文件中表述不一。
前者如桐乡“三治”。在探索中,“三治”的表述顺序改了好几轮。
卢跃东坦承,最初讨论时争议很大。他想把自治放在最前面,强调让百姓自己管自己。但有人不认可,认为基层组织都“自治”了,“那把党委、政府置于何地?风险较大”。最后,他把“德治”挪到了第一位,认为“德治”是基础。
2014年,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依法治国”话题。之后,浙江推广桐乡“三治”时,又把“法治”提到了首位。
等到2017年,十九大报告提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后,浙江又重新校准提法,将顺序调整为自治、法治、德治。
不只是顺序,每个词的内涵也在不断打磨。
“三治”试验刚启动,就吸引了公共管理学者、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郁建兴教授的关注。他多次到桐乡调研,了解如何让“德治”既能落地,又不越界。
郁建兴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回忆,他提醒当地主政者,“德治”必须在“法治”的框架下践行,是法律边界内的道德评判。而且这个“德”一定是现代社会主义的新道德,不是那些旧道德。
相比桐乡“三治”更多是理念和方式的调整,瑞安“三位一体”的博弈要复杂得多。在陈林看来,它涉及生产、供销、信用三大领域,触及部门权责与利益边界。
他记得,“三位一体”在全国推广时,有省市县乡村各级书记来找他,第一个问题都是,谁牵头、谁主管?
这不是新问题,背后是既有权力的再分配。“这是个怪圈。各涉农部门相持不下,要么都不干,要么只想自己干。”陈林说。
后来,“三位一体”两次写入中央一号文件,表述却有差异。2017年的表述是,加强农民合作社规范化建设,积极发展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合作。2021年又提出“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开展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合作试点”。
3
“去情景、提内核”
如果把视角拉远,不难发现,中央对地方农村领域改革试点的重视,早已有之。
1987年,农村改革走到了十字路口,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不再聚焦“三农”。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主任杜鹰,此时正在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任职,2019年接受《农村工作通讯》采访时回忆,当时大家很迷茫,“接下来改什么、怎么改、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在哪儿?”
“分区突破,分散风险”的理念这时被提了出来。
1987年,中央出台《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文件,明确提出“有计划地建立改革试验区”。同年7月,国务院批准建立首批14个农改试验区。开展了以土地为中心的股份合作制试点的广东南海;最早提出“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稳定了土地承包关系的贵州湄潭;孕育了农村股份合作制的浙江温州……这些后来耳熟能详的改革模式,均在其中。
这就是被“三农”学者温铁军称为“分区试验”的农村新政。
为了指导试验区改革,中央专门设立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温铁军当时负责项目审批前期调研,跑了多个不同类型的试验区。
温铁军曾撰文回忆试验区的“试验”路径:为制定土地政策选择试点时,贵州湄潭、江苏、山东、广东南海被同时纳入视野——湄潭在山区,土地细碎,调整空间有限;江苏乡镇企业发达,工业积累足以反哺农业;山东地处平原,适合规模经营;南海则是大城市近郊,农民收入主要靠工业。
“由此可以看出,当年一个制度调整的试验,我们要选至少3个不同地区。”温铁军在文章中写道。
当然,最终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的地方实践,并非都来自农改试验区。
2007年,成都、重庆获批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为较早启动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地区之一。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与对外开放研究所所长虞洪见证了当初的试点。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成都“大城市带大农村”特征明显,地区发展差异较大,城乡二元矛盾较突出,在全国具有代表性、典型性,最终获批试验。
试验启动后,成都宣布开展农村产权改革。改革要点是开展农村集体土地和房屋确权登记,推动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2008年5月,都江堰鹤鸣村在全国率先完成土地确权颁证。
成都摸索出的政策和方法,后来在中央一号文件中都能看到影子。“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就出现在了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的标题中。
在虞洪看来,地方经验“上行”之路从不单一,它们从四面八方汇入,经中央“去情景、提内核、再抽象”,最终淬炼为国家政策文本。
也是在2010年,农改区开始“重整旗鼓”。中央农办原主任陈锡文在接受《农村工作通讯》采访时回忆,之所以重启农村改革试验区,“是因为农村改革开始步入深水区,很多事情没有经过认真研究、没有经过实践检验,拿不准”。
于是,中央建立了由19个部委作为成员单位组成的农村改革试验区工作联席会议。同年10月,原农业部印发《农村改革试验区工作运行管理办法》,完善了试验区工作制度体系,2021年修订为《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运行管理办法》。
2018年发布《关于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改革试验区改革试验成果转化情况的通报》显示,共收录了68项试验内容的84项试验成果,其中包括中央文件12件。

2026年2月1日,广西南宁市宾阳县王灵镇东湖农场,农民在采收胡萝卜。(视觉中国/供图)
4
“写什么,怎么写”
事实上,由于发展阶段不同,农村改革的运行逻辑也在发生变化。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陈荣卓从事城乡治理研究,在《中国农村改革试点的运行过程与逻辑理路》一文中,他写道:“与改革开放初期‘不断试错'的大规模试验不同,‘顶层设计'成为深化改革的重要概念。”
虞洪也认为,与1980年代相比,当前的农村改革试验已是另一番光景,任务不同,背景不同,定位也不同,法律体系已基本完善,“一些需要突破现行法律的改革试点,要通过全国人大授权”。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就是典型案例。
2015年初,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在33个地方试水农村改革,授权这些试点区域可以在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管理制度等方面,暂时调整实施土地管理法有关法律规定。广东南海、四川郫县(现郫都区)等地都在名单上。
随着试点不断推进,边界逐渐清晰。4年后,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全面推开“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
相比之下,同年授权试点的宅基地制度改革,在当年中央一号文件中的表述却审慎得多——“稳慎推进”。
虞洪分析,这种表述差异藏着深层考量:宅基地制度改革事关重大,涉及农民基本居住权益,风险外溢性强,各方对改革路径尚未形成共识,仍需通过试点深入探索。“一号文件里的用词,也能侧面反映某些制度在地方的试点进展。”他说,“写什么,怎么写,都有考究。”
另一方面,地方试验内容如果不涉及突破法律,就可以大胆试、大胆闯,即便不属于试验区。虞洪补充道:“法无禁止即可为,鼓励基层主动探索创新。”
回顾近些年的“三农”改革,多位受访学者提到,以农村改革试验区为载体的试点实践,呈现出自上而下高位推动的“设计试验”特征。
这不免引发担忧:地方自主改革动力是否不足?
杜鹰还兼任过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主任。2019年,他在接受《农村工作通讯》采访时直言,现在“自下而上”还很不够,鼓励创造创新的环境还要大大改善。尤其对试验区而言,要有容错机制,试验项目和主题定了,方案也批复了,就要允许基层去闯。错了,再改回来。
在虞洪看来,“三农”改革目前已进入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协同、主动赋能与倒逼融合的混改阶段。他建议,在这一背景下,要给基层创造宽松的环境,中央划定大框架,允许基层自主选择改革任务、敢于探路。
“这些年,我们过于习惯制定政策,却很少真正静下心来‘解剖麻雀’。”“三农”问题学者李昌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真正有效的政策,离不开一场大规模、系统性的“千村调研”。
2021年6月,有着“改革四君子”之称的翁永曦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1980年代中央一号文件的起草过程。当时,他到安徽凤阳兼任县委书记,每天直面“三农”现实问题,必须脚踏实地去调研。调研后回到桌上讨论,大家聊的先不是“我认为”,而是“我去哪儿了,看到了什么,之后才是看法”。
把从调研中得到的基层创新梳理、总结,最终上升为国家政策。翁永曦说,农村改革既要“庙堂之策”,也要“市井之行”。
天载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 上一篇:配资网平台 奉劝大家:过年别买这6种年货,全都是科技,白送都别要!
- 下一篇:没有了







